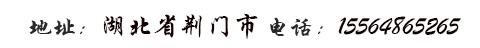虎毒不食子,她为何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
|
今天,广州某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是被害人的亲生母亲,她下手杀了自己的孩子。 “我儿子出生于年,我照顾了他46年,他是早产儿,大脑发育不良,还有软骨症,不会说话,生活不能自理。” “当他长大到三十多岁时,大脑衰退加快,身体越来越差,后来臀部肌肉萎缩,连坐都不能坐,只能常年卧床,后背都长了肉疮。” “他很痛苦,我也很痛苦。” “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我很辛苦。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担心自己先他离去。” “一个星期前,我思想斗争了很久,产生了喂他吃安眠药、让他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弄死他的念头。” 当这位83岁的母亲,在法庭上说出这样的话时,旁听群众无法不为之动容落泪。要让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是多么的惊悚,多么的不可想象。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呢,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呢? 但是这位特殊的孩子无法满足一个母亲的愿望。 “把他生成这样,是我自己对不起他,害他受苦。我宁愿自己犯罪,结束了他痛苦的人生,好过他生不如死。” “我的大儿子是正常人,但我也不能把他交给我的大儿子照顾,不能让大儿子承受如此大的负担。” “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嫌弃过他,也没有放弃过他,只是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起照顾他的重担。” 被告人的儿子、儿媳及部分亲属向法院写求情信,希望对被告人从轻处理。连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亦称:“被告人的行为法不可恕,但却情有可原。” 法院当庭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最终法院决定对黄某某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宣判后,控辩双方一致表示对该判决没有异议。 毋庸置疑,这是一份既不失法度又充满温情的判决,感谢广州法院在冰冷的法律下,给民众一份温暖的判决,为我们的法治增添了一分人文关怀,为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文化传统做出了新的诠释。 在刑事审判实务中,常遇到一些虽触犯严重罪名,但存在值得同情或可原谅情节的案件,如何处置此类案件在实践中常有争议。此类案件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应区分具体情节,不应按照普通犯罪来处理,应当从宽处罚,甚至是不认定犯罪。 司法程序的启动,本身就是一个对行为人惩戒、教育和改造的过程,已彰显了刑法之目的,揭示了法律之威严。未必一定要不加区别的贴上“罪犯”标签,或施以严刑峻罚。对此类犯罪的从宽发落,既折射司法刚性背后的柔情,又考验司法机关的智慧。 “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性质中产生出来的”,这是那个闻名遐迩的法国人让?雅克?卢梭说的,他说过一万句超级深刻的话,但在我看来,这是那一万句中最最深刻和最无可辩驳的。 中国自古就有“恤刑”的传统,“哀矜折狱”之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传承,深深的影响了中华民族,这也是中华法系最杰出的法制贡献之一。 在传统儒家看来,“仁”是个人道德的最高理想,其基本涵义是仁慈、礼让和友爱,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礼”不光是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还是日常的行为规范和指南。“仁”与“礼”的结合,实际表征出来的正是一种“善与公正的艺术”,这位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萨斯论唯一给我震撼的话语。 法院的判决既要体现现代法治的平等精神,也要契合传统文化的情感需要,不但要追求形式上的正义,更要实现实质上的正义。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为了满足那种呼之欲出的情感宣泄,还需要牺牲法律的通常形态,寻求一种符合大众情感的处理方式,而不是生搬硬套冷冰冰的僵硬法条。就如同公园大妈打气球案,按照现有法律,判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全国人民能答应吗?能符合人民群众的感情吗? 一个国家法律文本所体现的意志,与普通民众的情感并非完全一致。传统中国的报应主义思想,很明显与现代法治思想中的反对私力救济相冲突;传统中国的亲亲相隐、大义灭亲等为情感和道德所支持的行为,往往也为现代法治所摒弃。 在传统中国,可以通过“同居相隐不为罪”、“亲亲得相首匿”等制度设计来为那些情感上的正义寻找出路和归宿,以此来对抗法律的否定评价。但进入近现代,上述制度被驱逐出官方的法律文本。 文字性的制度可以轻易通过法律的修订从文本中抹去,但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社会客观情势和人类情感、传统却无法抹灭,如果情感上的正义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和宣泄,社会又能靠什么维系下去呢? 回到开篇的这个案件,羁押她,给公众的心灵关上一道冰冷的门;放了她,还社会道德一个温情的通道。 老爹有说法,有理有法有人情、有趣有料有逼格 本文为老爹原创,转载请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aochanera.com/zcewy/760.html
- 上一篇文章: 毛泽东全部子孙的照片,绝版
- 下一篇文章: 今天,你被这张照片刷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