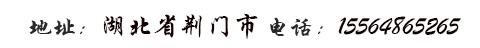物华佛光里的太阳神
|
全国治白癜风最好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160725/4910787.html 黄地卷云太阳神锦 年代:北朝 尺寸:长84厘米,宽62厘米 文物编号:QK 组织结构:平纹经锦 出土地点: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 收藏机构: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 都兰所出太阳神锦计有3件,均出于热水一号大墓,此为其一。此锦为1:1平纹经重组织,经纬线均无捻,本色纬线,以红、黄两色经线显花。织锦作簇四骨架,并于经向的骨架联接处用兽面辅首作纽,而在纬向的连接处则以八出小花作纽。织锦全幅应由三个团窠连接而成,作为主题纹样的太阳神团窠居中,狩猎团窠于太阳神团窠上下各一,两者皆残。 太阳神团窠的主体为六匹翼马所牵引的马车上之太阳神。马车作四轮,有车厢。太阳神作正面形象,头戴宝冠,手施禅定印,交脚坐于莲座之上。项后附背光,头顶施伞盖,两侧各悬龙首幡。太阳神身后左右各两童子,二人持斧钺,二人持长柄叉。太阳神团窠之间织有汉字“吉”字。太阳神团窠上下当为狩猎团窠,残存部分第一组为骑驼猎狮,第二组为骑马射鹿。猎手都作返身回射之状,此即“安息射”(Parthianshot)。狩猎团窠之间织有汉字“昌”字。 太阳神锦及其局部青海都兰一号大墓出土 都兰一号大墓概况 青海省都兰县夏日哈到巴隆之间的狭长地带,分布有众多吐谷浑王国和吐谷浑邦国时期(吐蕃时期)的古墓,仅热水沟内不到1公里长的地带就有近座古墓。热水沟地区的古墓沿察汗乌苏河南北排布,北岸余座,南岸30余座。热水一号大墓北依血渭山脚(故又名血渭一号大墓),南临察汗乌苏河,整个墓地以之为中心沿山麓向两翼排布。热水一号大墓上层封堆顶部到南面地平面高度达35米,堪称当地乃至青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吐蕃时期墓地。—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及其附属遗址进行了发掘。经考古发掘,发现封土顶下4.5米深处有一长方形动物殉葬坑,埋有牛、羊、狗、鹿、马等动物。封土下11.5米处为墓室,平面呈十字形,东西长21米,南北长18.5米,由墓道、墓门、回廊、东室、西室、中室和南室组成。中室为木室,大量的丝织品残片即出土于此,其他各室均为石室,未见人骨。大墓南面平地上另有动物殉葬遗迹,居中为5条殉葬沟,殉马87匹,东西两侧则为27个圆形殉葬坑,殉有牛、狗等(许新国,6)。 大墓的年代,因墓中并无任何有明确纪年的遗物出土,只能通过对其出土遗物的考察来作推断。许新国、赵丰通过对大墓所出丝织品的研究,指出这些丝织品大体可分四期:北朝晚期、隋代前后、初唐时期和盛唐时期,第四期的时间约在7世纪末到开元天宝时期(许新国、赵丰,)。仝涛通过对大墓所出的丝绸、镀金舍利银器、金带饰等的考察,将大墓的年代置于7世纪末到8世纪初之间(仝涛,)。关于墓主人,许新国认为是吐蕃时期吐谷浑邦国的国王(许新国,9),汪涛推测为松赞干布的大论禄东赞(汪涛,,转引自仝涛),霍巍提出四种可能:吐蕃所立吐谷浑小王之类的王室贵族、下嫁吐谷浑的吐蕃公主、已投降归顺吐蕃的吐谷浑原王室残部、受吐蕃支配的吐谷浑军事首领(霍巍,3),仝涛则进一步以为是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仝涛,)。 太阳神锦的纹样 关于太阳神锦,赵丰(赵丰,)、许新国(许新国,)、康马泰(MatteoCompareti,康马泰,0)等人都作过专门研究,如他们所指出的,此织锦上的太阳神形象乃是出自异域。太阳神在古希腊、西亚、中亚、印度很早就已流行。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其常见的就是其驾乘四匹马牵引的马车之形象。大约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时,驾乘马车的太阳神形象也来到中亚和印度北部地区,从而被祆教和佛教等吸收。目前所知,现今所见的太阳神相关的图像,主要分布于中亚地区且与佛教关系密切。 克孜尔石窟34窟日天壁画 库木吐喇石窟23窟日天壁画 巴米扬石窟东大佛 巴米扬石窟东大佛龛顶日天壁画局部 巴米扬石窟东大佛及其龛顶日天壁画复原图葛达尔夫人(MadamGodard)摹绘 太阳神的形象,目前可知最为集中的乃是见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于石窟寺中,太阳神乃作为佛教中的日天而出现。朱天舒曾指出日天见于克孜尔石窟的8、34、38、97、98、、窟壁画,在这组洞窟中,日天乃与月天、立佛一同出现,且多数与风神和迦楼罗并见(朱天舒,3)。克孜尔石窟之外,日天形象还见于库木吐喇石窟23、31、46窟,敦煌莫高窟窟(藏经洞所出绢画上亦见有日天、月天形象),阿富汗巴米扬石窟K、M窟及主窟东区东大佛龛顶壁画。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织锦、壁画上的太阳神形象有繁简之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青海都兰所出织锦上的太阳神非常明显地与巴米扬东大佛龛顶壁画上的太阳神接近。这一太阳神的形象,很巧合地见于罽宾般若力所译的《迦楼罗及诸天密言经》。此经述“迦楼罗画像法”云: 日天作天王形,被甲于金车上交胫而坐,以四匹花聪马驾之,马首两左两右。日天左手持越斧,下抚左边青衣童子头,右上手持三股长柄叉,下手抚右傍青衣童子首。车厢内日天前有一小童子,而作金色御马也。天王发黑色,蠡髺宝冠,身首皆有圆光,外以日轮环之。日轮赤色,文如车轮。二青衣童子并御马,于车厢内立,出胸已上。日天首光青,身光像色也。 又,《成菩提集》卷四引《梵天七曜经》云“其形准梵本如菩萨身,住赫奕日轮中,面门含笑,顶上圆光,五色间杂,坐宝莲花,花底以五碧宝马驾车。……首戴宝冠,无花鬘严身,跏趺而坐,合掌持莲花”。据此可知,西域石窟寺中的太阳神,其造型大抵本诸佛经,乃是作为佛教中的诸天而存在。希腊神话人物在其东传的过程中被吸纳入佛教,太阳神并非独例(邢义田,4)。 阿富汗哈达佛寺中被吸纳入佛教的赫拉克利斯 织锦所反映的西域交通 前面提及太阳神多见于巴米扬、龟兹等地的石窟寺中,在论及石窟寺时,宿白曾以为开凿大像窟和雕塑大型立佛或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一个特点,并进而说道“这个推测,如果可以成立,则龟兹型的佛教文化除了具其他类型的石窟形制和壁画外,还有一个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这个重要内容。这个重要内容,给予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当比其他类型的石窟形制和壁画的影响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巴米扬石窟壁画上所见的含绶鸟、野猪纹同样见于克孜尔60窟、吐峪沟千佛洞38窟。而含绶鸟纹锦则在青海都兰墓、新疆阿斯塔那墓中都有出土,野猪纹锦虽不见于青海都兰墓中,但在新疆阿斯塔那墓中有不少出土。事实上,与巴米扬大佛建立有关的路线业经桑山正进研究指明(桑山正进,),其中《迦楼罗及诸天密言经》译者般若力所在的罽宾乃是此路线的枢纽,而处于此路线东部的龟兹无疑也是一个重镇。 巴米扬石窟D窟联珠团窠含绶鸟纹壁画 克孜尔石窟60窟联珠团窠含绶鸟纹壁画 巴米扬石窟D窟野猪头壁画 吐峪沟千佛洞38窟野猪头壁画格伦威德尔摹绘 含绶鸟纹锦衣,传为盗自青海都兰,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野猪纹锦 无独有偶,青海都兰墓地之外,太阳神锦还见于新疆阿斯塔那墓中。两处墓地所出,织锦纹样一致的还有胡人牵驼、含绶鸟、联珠对龙、对马、对羊、宝花等。分处异地的两处墓地,出土的织锦多有相同,不免使人联想当时两地往来的亲密程度。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所控制的地区乃南朝与西域交通的要道,使者、商人、僧侣往来其间,这已为中外学人所指出。早年吐鲁番曾出有《妙法莲华经》,其卷尾上题“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萧道成,普为一切,敬造供养”。经唐长孺考证,萧道成称帝前之写经当为刘宋使者王洪轨携至高昌。升明二年(),王洪轨取道高昌出使柔然,约为共击北魏,遂施此经(唐长孺,)。即使在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之后,穿越吐谷浑领地的河南道仍发挥重要作用。 高昌所出《妙法莲华经》上萧道成篡政即位前夕的写经题记 至于高昌和龟兹之间,则关系至密。仅就织锦而言,吐鲁番文书所见有高昌锦、丘慈(龟兹)锦、疏勒锦、提婆锦,且均为高昌织造(吴震,9)。丘慈锦,唐长孺以为“高昌、丘慈都生产锦,大概这种‘绵经绵纬’的锦始于丘慈,因此即以丘慈命名。丘慈锦似乎在高昌销行较广,所以为高昌所仿制”,又云“高昌人仿制丘慈锦,与这种‘绵经绵纬’的锦在高昌流行,疑亦与宗教有关,不仅贸易往来”(唐长孺,)。横张和子、坂本和子也曾探讨龟兹锦的产地及其特点,二人认为龟兹锦最早产于龟兹而后乃被高昌所仿制(横张和子,;坂本和子,8),龟兹锦当属平纹纬锦,横张和子且举了可能是龟兹锦的实例。与唐长孺等人所论不同,武敏认为丘慈锦只是仿了龟兹毛织物纹样而已,而龟兹未必已能生产丝质织锦(武敏,;武敏,)。吴震看法与武敏一致,认为“龟兹锦、波斯锦、疏勒锦均是高昌织造,因各自纹样风格不同而得名”(吴震,9)。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提婆锦,吴震以为或即都兰所出太阳神锦(吴震,9)。 参考文献 阿米·海勒著,霍川译:《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3年第3期。 何恩之撰,赵莉译:《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分期新论补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年第2期。 霍巍:《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3年第3期。 李朝、柳春诚:《都兰热水一号大墓考古研究的重大收获——兼与仝涛先生商榷》,《中国土族》年第4期。 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巴米扬·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敦煌研究》年第2期。 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7年第2期。 桑山正进著,徐朝龙译:《与巴米扬大佛的建立有关的两条路线(上)》,《文博》年第2期。 桑山正进著,徐朝龙译:《与巴米扬大佛的建立有关的两条路线(下)》,《文博》年第3期。 桑山正进著,王钺编译:《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敦煌学辑刊》年第1期。 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份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年,第21—38页。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年,第—页。 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山居存稿》,中华书局,年,第—页。 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年第4期。 邢义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4年,第15—47页。 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年第3期。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年第15、16期,第63—81页。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6年,第-页。 许新国:《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9年第4期。 张元林:《论莫高窟第窟日天图像的粟特艺术源流》,《敦煌学辑刊》7年第3期。 赵丰:《魏唐织锦中的异域神祇》,《考古》年第2期。 赵莉:《克孜尔石窟分期年代研究综述》,《敦煌学辑刊》2年第1期 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年第6期。 廖旸:《克孜尔石窟壁画分期与年代问题研究》,《龟兹学研究》第一辑,新疆大学出版社,6年,第—页。 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年第5期。 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年第2期。 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丝织品考辨》,《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年,第—页。 横张和子:「吐魯番文書に見える丘慈錦と疏勒錦について」,『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XIII,年,第—页。 坂本和子:「织物に见るシルクロードの文化交流トゥルファン出土资料─锦绫を中心に」,大阪大学博士论文,平成二十年(8年),第64—67页。 AngelaSheng,WovenMotifsinTurfanSilks:ChineseorIranian?Orientations,30.4,,pp.45-52. MatteoCompareti,IranianDivinitiesintheDecorationofSomeDulanandAstanaSilks,AnnalidiCaFoscari.RivistadellaFacoltadiLingueeLetteratureStranieredellUniversitadiVenezia,XXXIX.3,0,pp.-. MatteoCompareti,TheroleoftheSogdianColoniesinthediffusionofthepearlroundelspattern,ērānudAnērān:StudiespresentedtoBorisIlichMarshakontheOccasionofHis70thBirthday,3,pp.-. TianshuZhu,TheSunGodandtheWindDeityatKizil,ērānudAnērān:StudiespresentedtoBorisIlichMarshakontheOccasionofHis70thBirthday,3,pp.-. 撰文|乐浪公审稿|阿印 图片资料来自网络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到其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aochanera.com/zcewy/17565.html
- 上一篇文章: 父母一顿操作,台州宝宝换血才保命新生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